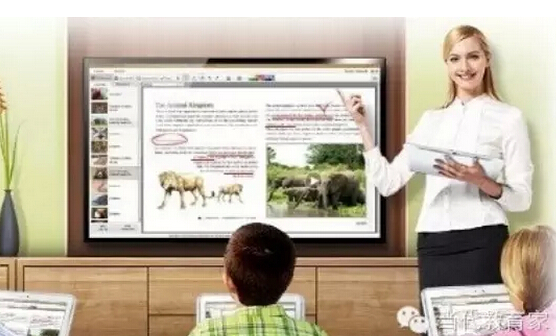
2006年9月,一个人,只有一台电脑的Khan Academy创建了可汗学院,如今已拥有1000万学生;2010年5月,开放式在线教育网站Udemy创建,并在2个月内拥有2000门课程1万名注册用户;2012年2月,计算机科学领域的网络学习社区Udacity创建,一个月内9万名学生注册,覆盖190多个国家;2012年4月Coursera、edX创建,在线教育正式进入MOOC时代……
我相信,网络会像冲击出版、新闻、商业等领域一样,冲击学习领域。新一轮的学习革命,正在向我们走来。
我认为,不能把“学习革命”仅仅理解为借助新技术向学习者提供更丰富的学习资源。这算不上“革命”,充其量只是一种改善,一种改良。标志学习革命的关键词应有五个:自主学习、个性化学习、认知诊断、批判性思维和教育增值。
自主学习
很多年前,我听过一个教育讲座,一个澳大利亚的中学物理教师讲:我教了30年的物理课。第一个10年,我是“教物理”;第二个10年,我是“教探索”;第三个10年,我不再是“教”学生如何探索,而是“支持学生自己去探索”。在他物理教学的第3个10年中,他完成了从“教师主导”向“学生自主”的转变。
“教师主导”的教育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传统之中。“尊师”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特征要素,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在中国,早上妈妈把孩子送到学校门口时常常会说“好好学习,听老师的话”。在一些西方国家,妈妈在把孩子送到学校门口时常常会说“精彩地过上一天(have a great day)”。
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终身教授、经济学家陈志武在发表于《南都周刊》2008年第253期的一篇文章中讲述了自己在美国长期生活和伴随两个女儿长大的经历。他写到她的女儿“在小学做的研究与写作跟我当教授做的事情,性质差不多,我做研究上网要找资料,而她也是为每个题目上网找资料、做研究,她写文章的训练也已经很多。在小学做的研究与写作跟我当教授做的事情,性质差不多”。
我曾听到过许多像陈志武这样的华人父母们感叹美国的教育,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与自己小时候在国内接受中小学教育时相比,美国儿童具有更强的自主性。
我们需要认识到,“尊师”的中华文化传统今天已经成为我国人力资源开发的阻力。为了跟上新一轮学习的学习革命,为了开发我国的人力资源,需要重新思考学习过程中教师的作用,需要更多地鼓励学生依靠网络的支持进行自主的探索性学习。
把学生从“配角”变成“主角”,把曾经是主角的“教师”变成作为配角的“助学”。这样,才能够算“学习革命”。
个性化学习
2009年10月28日,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汉语教师培训中心主任奥登(Jane Orton)博士与北京语言大学教育测量研究所的研究生们进行了一次座谈。座谈中奥登博士谈了一个观点:个性化化教学植根于西方的文化传统之中。个性主义(individualism)与基督教、天主教和犹太教的文化传统有关。按照基督教的教义,不论穷富,不论国王或乞丐,不论教授或文盲,一个人进天堂或进地狱,完全要由他自己决定。这里,父母、老师、牧师的努力,任何其他人的努力,都不能替代。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都要为行为的后果负责。只有你一个人能够把自己送进天堂,别人都不能替代。
奥登博士的观点尚可以讨论,但她的看法可以为我们带来一些启发。伴随工业化过程出现的现代学校,确实提高了教育的效率。由于教师职业资格制度的形成,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教育的质量。但是,付出的代价是学习过程中个性的丧失。
学生不是一只通过训练就可以获得某种能力的“巴甫洛夫的狗”或“斯金纳的鸽子”,学生是一个有好奇心、有求知欲、有情感的人。学生们拥有不同的性别、成长经历、生活环境以及智力和心理发展的水平,他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并不是统一的教科书和统一的课堂教学可以满足的。不同的学生需要借助不同的学习资料以不同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来完善自己的人格,来发展自己的能力。
尊重学生之间的个别差异,尊重学生的个性,把像工厂生产标准化产品一样生产统一规格的毕业生的过程,把像马戏团训练小狗整齐划一地表演节目一样的过程,变为个性化的学习。这样,才能够算“学习革命”。
认知诊断
近几年,认知诊断(cognitivediagnosis,常被简称为CD)是教育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热门话题,大量的博士、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将认知诊断作为研究课题。
传统的考试仅仅报告一个总分。获得相同总分的人,可能具有不同的认知结构和过程。认知诊断研究将认知心理学和心理测量学结合,借助现代的统计方法和计算机技术,对学生的认知结构和认知过程进行个性化的诊断分析,向学生、教师和家长提供更丰富的反馈信息,对进一步的学习和教学提出更具体、更有针对性的建议。认知诊断过程可以发现每个学习者的知识掌握状况,发现每个学习者的认知结构,并提出补救建议。
只有借助现代的统计工具、高速计算机和网络环境,才可能根据每个考生在考试中的反应做出认知诊断。今天,已经发展出多种认知诊断的数学模型,包括规则空间模型、统一模型、融合模型、DINA模型、属性层级模型,等等。
根据认知诊断的观点,考试不应仅仅提供一个笼统的“总分”,而应该进行描述性计分(descriptive
scoring)。例如,美国教育测验服务中心(ETS)在美国的“高考”——《学术评估测试(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
SAT)》中,在《初级学术评估测验(Preliminary 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PSAT)》中,都采用了描述性计分系统。这一系统不是仅仅报告总分,而是力图向考生、教师、家长提供关于考生的优点和不足的更丰富的诊断信息。
描述性记分的关键步骤是对测验所要测量的能力进行特征(feature)定义,定义这种能力所具有的属性(Attribute),详细描述学习的进程,界定不同的认知模式和不同的问题解决路径。
借助网络、测量技术和计算技术,向学生、教师和家长提供及时的、有针对性的认知诊断服务,才能够算“学习革命”。
审辩式思维
以往,在评估一所学校优劣时,人们关注的是“投入(input)”,是学校投入了多少经费,有多少教学设备,有多少高学历、高职称的教师,学生的平均录取成绩如何,等等。今天,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在评估一所学校时,应该更多地关注“产出(output)”。今天,人们更多地关注基于“产出”的教育评估。
为了对“产出”进行评估,由520所公立大学组成的美国州立大学联盟(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t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AASCU)和公立大学联盟(Association of Public andLand-grant Universities,APLU)共同推出了一个对高等教育进行评估的“自愿问责系统(Voluntary System of Accountability,VSA)”。在VSA中,定义了“核心教育成果(Core Educational Outcomes)”。核心教育成果包含4个部分:审辩式思维(Critical thinking)、分析性推理(Analytical reasoning)、阅读(Reading)和写作(Writing)。
伴随网络的发展,获取某种特定知识越来越容易。以往,为了查找某一个资料,我们可能要在图书馆中寻找许多天,今天,借助搜索引擎,我们可以信手拈来。今天,重要的已经不是对特定知识的记忆,不是向学生灌输一些特定知识,而是发展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伴随思考的深入,人们发现,对于一个理论、一个观点、一个命题的论证,不是一个可能立即得到答案的实验室研究,不是一场可以决出胜负的球赛。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了百年。今天,辛亥革命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仍然是激烈争论的话题。“五四”已经过去了近百年。今天,“五四”对于中华民族文化建设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仍然是学术界激烈争论的话题。“罗斯福新政”已经过去了近80年。今天,对其得失成败仍然存在巨大争议。人们发现,一个新理论、新观点被接受,一个旧理论、旧观点被放弃,往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往往是一个旷日持久的论证过程。持有某种观点的人完全将自己的论辩对手说服的情况很少,持有某种观点的人将所有的论辩对手说服的情况也很少。
今天,中国学校中广泛流行的是形成于上世纪50年代的学习方法,是深受前苏联影响的学习方法。学校中广泛流行的是形成于20世纪以前的“真理——谬误”的简单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把学习过程理解为一个学生学习和掌握“科学真理”的过程,理解为一个老师向学生传授“科学真理”的过程。事实上,在今天的学校中讲授的许多标有“科学真理”标签的东西都是非常可疑的。这种学习方式,大大地摧残了学习者的好奇心,大大地打击了学习者的怀疑精神,大大地压抑了学习者的创造性。
改变这种陈旧的学习方式,不再是简单地向学生灌输特定的结论,而是倡导研究性的学习,发展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使学习成为一个探索和发现的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个记忆和拷贝的过程。这样,才能算是“学习革命”。
教育增值
近几年,“增值(Value-added)”成为教育领域中的热门话题。人们认识到,由于学生的原有基础不同,仅仅根据一个学习阶段的结业水平对学生、教师和学校进行评价是不合理的。相对于一个学习阶段结束时的终结性评价,“增值评价”更重要。在学习中,需要更多地关注学生经过学习以后获得了多大程度的进步和增值,需要关注教师和学校在帮助学生获得增值方面所发挥的实际作用。
在上面谈到的美国两个大学联盟共同推广的“自愿问责系统(VSA)”中,就包含一套关于“增值”的测试和计算方法。根据这种方法,在学生入学和毕业时向同一组学生进行一项反映“核心教育成果”的测试。通过计算两次的成绩差异,对学生的“增值”情况进行评价。
增值固然是一种教育评价技术,更是一种学习理念。如果以学习的“增值”理念来审视今天的学校教育,不难发现,即使在一些办学条件很好的学校中,增值效应也是很有限的。对于许多儿童,一个学期中所学的语文知识和算术知识,他或她在学期开始的时候,其实已经掌握了。一个学期的课堂学习,对于这些儿童的增值效应是很有限的。
其实,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中国教育改革的一些先驱者就已经意识到“教育增值”的问题。大约在1960年5月,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小学的领导安排正在读小学2年级的笔者跳班到3年级。他们知道,笔者当时已经完全掌握了小学2年级教学大纲中包含的教学内容,如果让笔者继续留在2年级学习,学习增值效应几乎是零,这对于笔者无疑是一种生命的浪费。于是,笔者成为了一个获得了更多学习增值机会的幸运儿。与同时进入小学的同学们相比,笔者提前一年结束了小学的学习。半个世纪后的今天,难道不应该让更多的儿童像当年的笔者一样成为幸运儿吗?难道不应该让更多的儿童获得更大的学习增值的机会吗?
教育机关所关注的不仅仅是每个学生是否掌握了教学大纲中所规定的内容,而是关注是否每个学生都获得了增值的机会。这样,才能算是“学习革命”。
